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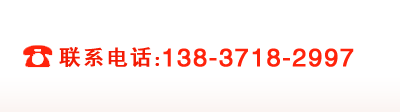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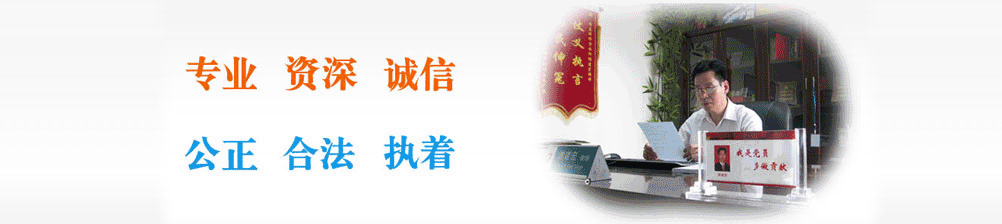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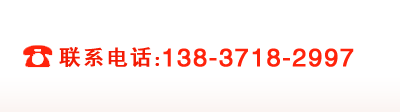
律师按语:这是发生在河南省某县城里一个真实的案例,是我和娄珍杰律师正在办理的一个案件,本文中有关当事人和证人的真实姓名已作了化名处理,在姓名上如有类同的,纯属偶然巧合。由于该案件牵扯到扫黄问题,因此,在当地的小县城里影响很大。涉案有三名被告人,其中一名是当地人,另外两名都是外省人,我们为其辩护的被告人蒋明锡(化名)是外省人即本案的第一被告人。我们律师在阅卷后向承办法官表明了将作无罪辩护的观点,可能在五月份中旬或下旬要确定开庭时间,正好借助疫情居家办公,我们认真书写了这份辩护词,并确信我们的辩护理由是合乎案件事实、有理有据的 . . . . . .
蒋明锡(化名)被控组织卖淫案一审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河南红达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蒋明锡近亲属的委托,指派我担任蒋明锡的辩护律师之一。接受指派后,辩护人通过远程视频会见了被告人蒋明锡,并认真查阅了本案的全部卷宗材料,今天,我们又参加了法庭调查,案件事实我们已经了解清楚。辩护人认为此案不属于刑事案件,被告人蒋明锡的行为也不构成组织卖淫罪。在没有发表详尽的辩护意见之前,辩护人根据本案的事实情况以及目前的刑事法律规定,认为以下几个问题需要向法庭表明:一、“手淫、口交、胸推”这些色情服务项目属不属于我国刑法规定的卖淫行为;二、出资的合伙人如果不知情或者不参与经营管理,是否要对他人的管理行为承担责任;三、蒋明锡在本案中的行为是否符合我国刑法规定的组织卖淫罪中的组织特征;四、四方休闲会所(以下简称四方会所)店内的日常管理人带领技师私自外出卖淫的行为,是否属于单位行为;以上这些问题不但是本案争议的焦点,也是本案需要查明的问题,否则,就难以正确定性和适用法律。下面,我们针对这些问题发表辩护意见:
一、根据当前的刑法和刑事司法解释,没有明文规定“手淫、口交、胸推”等色情服务的内容属于我国刑法中的卖淫行为。
根据四方会所日常管理人董超阳、前台江玲玲以及五名技师的笔录,我们可以明确一个事实:四方会所内不提供性交服务,提供的是按摩、足疗这些保键服务以及手淫、口交、胸推等色情服务。因此,首先要明确“手淫、口交、胸推”等行为,是否属于刑法规定的卖淫行为。
辩护人认为,手淫、口交、胸推,这些属于是色情服务,而不是卖淫行为,卖淫是指为了获取物质报酬(金钱、礼物等),以交换的方式有代价的或有接受代价之约的与不固定的对象发生的性行为,卖淫是直接肉体接触,这种肉体必须是男女双方的生殖器。虽然,按摩女的手抑或乳房也属于肉体,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性交,如果把色情服务作为卖淫,那么,组织卖淫罪必须重新归类,否则,就是没有法律依据。我国现行《刑法》及刑事司法解释,目前还没有明文把“口交、手淫、胸推等色情服务界定为刑法意义上的卖淫。因此,司法实践中对于如何认定刑法意义上的卖淫,应当依照刑法的基本含义,严格遵循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罪刑法定原则,否则,就会把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行政处罚行为与刑法对于犯罪的刑罚行为混为一团。
我国刑法规定的组织卖淫罪中的卖淫行为,在没有正式的法律和司法解释界定其内容之前,仅仅是指男女之间的性交行为。人民法院在审理有关卖淫案件时,不宜对刑法上的卖淫概念作扩大解释,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这是全世界的刑法都普遍遵守的原则。目前,由于我国的刑法及刑事司法解释并没有对卖淫的概念作出扩张性的解释,因此,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可以参考法律实务当中的一些指导性意见。如:国家法规数据库中的一则案例解析中,引用了最高人民法院在答复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口淫、手淫等行为能否作为组织他人卖淫罪中的卖淫行为时,明确答复,口交、手淫尚不属于组织他人卖淫罪中的“卖淫”。辩护人目前仍未找到这个批复的原文件,但能在国家法规数据库中引用的一定不会是虚构的。《(2000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刑二庭关于执行刑法若干问题的具体意见(三)》第11项意见:刑法分则第8章第8节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规定的“卖淫”,不包括性交以外的手淫、口淫等其他行为。《(2013年)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涉卖淫类刑事案件审判实务解答》:刑法分则第8章第8节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规定的“卖淫”,不包括性交以外的手淫、口淫等其他行为。再如: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研究室主任,第二巡回法庭分党组书记,庭长胡云腾在2016年写的《谈谦抑原则在办案中的运用》提出:多年以前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在起草关于组织、强迫卖淫犯罪的司法解释时,有种观点就主张对口交和“手淫 ”之类的色情行为解释为卖淫,但我们秉持谦抑的理念,没有对这种犯罪入刑,我至今认为这是正确的。以上这些均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参考。
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条规定的答复》称“卖淫嫖娼,一般是指异性之间通过金钱交易,一方向另一方提供性服务以满足对方性欲的行为。至于具体性行为采用什么方式,不影响对卖淫嫖娼行为的认定”。公安部在2001年2月18日作出公复字[2001]4号批复称“不特定的异性之间或者同性之间以金钱、财物为媒介发生不正当性关系的行为,包括口淫、手淫、鸡奸等行为,都属于卖淫嫖娼行为,对行为人应当依法处理”。以上两个批复性文件,都不可以作为本案的定罪量刑的依据,因为,公安机关无权进行司法解释,(公安机关既属于行政机关也属于司法机关)因此,公安部的批复只能作为处理违反治安管理给予行政处罚的依据,而不能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刑事案件定罪量刑的法律依据。况且,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批复》中已经明确该答复只是针对如何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条规定的答复,而不是针对人民法院如何适用刑法中组织卖淫罪的司法解释,这仅仅是明确了行政违法中“卖淫”概念,而违法不等于是犯罪,最高院对如何适用治安管理条例的答复以及公安部的批复不能作为本案的定罪依据,况且,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已经被废除了,上述两个答复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
二、蒋明锡的行为不符合我国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组织卖淫罪的构成要件,依法不能构成组织卖淫罪。
以上辩护理由说明,手淫、口交、胸推等色情服务并非是刑法意义上的卖淫行为。也就是说,截止目前,我国的刑法和司法解释还没有明文将上述色情服务列入到我国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一款组织卖淫罪的卖淫行为中。下面,我们将从退一步的角度上讲,假定“手淫、口交、胸推”等色情服务属于卖淫行为的话,那么,被告人蒋明锡也不构成组织卖淫罪,理由如下:
(一)在主观上,蒋明锡对四方会所存在的色情服务不知情,因此,蒋明锡没有组织他人卖淫的犯罪故意。
根据人民法院出版社组织编写的《公、检、法办案标准和实务指引》一书中关于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组织卖淫罪的学理解释认为“组织卖淫罪惩罚的是卖淫的组织者,而不是卖淫者”。这里的组织性,体现为对卖淫人员及卖淫活动起到了直接控制、管理和支配的作用,与组织者是否是卖淫场所的经营者和承包者没有必然的关联。同时,这种控制、管理应当是直接对准卖淫活动本身,而非仅在外围为组织、策划或为指挥卖淫提供帮助。组织卖淫罪与其他组织类犯罪相比,法定最低刑比较高(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这就要求我们对组织卖淫罪中的组织行为进行严格的解释,才能符合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关于是否组织、安排卖淫活动,主要是指组织者在卖淫活动中有无参与组织、安排具体的卖淫活动,具体方式有推荐、介绍、招揽嫖客、安排相关服务、提供”。以上这些虽然不属于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但也是刑事法律专业人员根据当前有关司法解释对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规定的组织卖淫罪所作的学理解释,对于我们在办案实务中是具有参考价值。
结合本案,被告人蒋明锡是四方会所的投资人之一,但四方会所是个体户性质的企业,不是公司性质的企业,并不是按照出资比例大小来确定投资人的实际控制权的。虽然蒋明锡的投资要比龙向飞、董超阳的多,但是,董超阳是四方会所的工商登记注册的经营者,也是四方会所实际的日常经营管理人,龙向飞是该所的财务管理人,而蒋明锡在四方会所里没有担当任何的职务。而且,由于蒋明锡不是西川县当地人,他的户口、家庭和主要经商地都是在深圳市,蒋明锡除了四方会所刚开业时在过店里有一个月的时间,除此之外,一直都在外地,他从不参与四方会所的经营管理,对于店内是否存在有色情服务更是不知情,因此,蒋明锡没有组织卖淫的组织故意。董超阳在公安机关作笔录时,说蒋明锡是老板,店里的事都向他汇报,这只是董超阳在案发后为了推卸责任的说法,空口无凭。而事实上,在四方会所的实际经营当中,都是董超阳一人说了算,因为,从龙向飞与董超阳的微信聊天记录就可以看出来,龙向飞提醒董超阳不让技师出去给客人提供服务,这就说明董超阳的经营管理是自主决定的。而在本案的卷宗材料当中,找不到有关董超阳和龙向飞关于店里的色情服务向蒋明锡汇报或者讨论过的有关证据材料,这说明,店内的经营在蒋明锡的脑子里属于是正常的经营,对其经营服务的项目,蒋明锡只知道有足疗、按摩、养生服务,但不知道有手淫、口交、胸推这些色情服务。店里的几个技师在她们的询问笔录中,说店里的色情服务作为老板们都是应该知道的,这种证言是带有猜测性质的,并不是确凿的事实证据,而且,几个技师的笔录中对于这一问题的问答内容,都是一模一样的文字内容,这明显是复制粘贴的内容,并不是技师们根据实际情况回答的内容,所以,技师们的询问笔录也不能确实充分的证明蒋明锡对店内技师提供服务的内容是知情的。
四方会所的日常经营管理人董超阳有时带领技师外出为客人提供服务,但蒋明锡对此也是不知情。蒋明锡不参与经营、管理,与会所内技师也没有直接的接触,更谈不上组织或控制技师从事卖淫活动的事实。因此,即使董超阳与技师存在有外出卖淫行为,也与蒋明锡不存在有刑法意义上的犯罪因果关系。综上,辩护人认为,蒋明锡对四方会所的色情服务不知情,本案的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蒋明锡具有组织卖淫的组织故意。
(二)在客观上,蒋明锡不具有我国刑法关于组织卖淫罪中组织他人卖淫的客观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一条规定“以招募、雇佣、纠集等手段,管理或者控制他人卖淫,卖淫人员在三人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规定的组织他人卖淫”。这就是司法解释关于刑法中的组织卖淫罪的客观行为表现。因此,组织卖淫罪的主体必须是卖淫人员的组织者,认定一个人是否构成组织卖淫罪,除了看他组织的是否是卖淫人员以及这些被组织的人员是否实施了卖淫行为,被告人在主观上具有组织他人卖淫的主观故意以外,还要看他是否有组织行为,且被组织的卖淫人数是否达到三人以上。蒋明锡在本案中不具有上述犯罪的事实要件,理由如下:
1、蒋明锡不存在招募、雇佣、纠集卖淫人员的行为。
辩护人不认为四方会所的技师属于是卖淫人员,如果法庭把四方会所的四名技师认定为司法解释中的“卖淫人员”的话,那么,根据案卷材料显示,四方会所的四名技师均是通过董超阳来到会所内上班的。会所技师刘蕾蕾与巩凡凡是董超阳主动添加其二人的微信,直接邀请她们到会所内上班的。这两人不但与蒋明锡没有任何的联系,而且她们至今都不认识蒋明锡。仝娅娅、孟小莉是自行到会所由董超阳接待同意其在会所当技师的。四方会所的技师除了龚秀娟外,其他的四名技师均不是蒋明锡招募、雇佣、纠集的,这四名技师和蒋明锡完全没有联系。龚秀娟笔录称看到招聘自行来到会所,当时是蒋明锡接待的她。首先,龚秀娟在会所不存在卖淫行为,不属于卖淫人员。其次,龚秀娟的笔录中称自己原来是从事足疗工作的,即便龚秀娟是蒋明锡招聘的,那么蒋明锡招聘的只是一名足疗技师,既不是卖淫人员又达不到三人以上,因此,蒋明锡的行为依法不符合组织卖淫罪的构成要件。
2、蒋明锡不存在管理、控制卖淫人员的行为。
首先,蒋明锡不参与四方会所的经营管理,且一直都不在店内,山高路远,对店内是无法进行控制和管理的,蒋明锡对店内所有的人员都不存在管理和控制的行为;其次,会所的前台以及四名技师都不认识蒋明锡,蒋明锡如何能与这四名技师形成领导与服从的关系呢?
3、蒋明锡接待的技师人数达不到三人以上。
四方会所的员工中,只有龚秀娟(666号技师)认识蒋明锡,由于龚秀娟是在四方会所开业时到会所的,当时蒋明锡在店里处理开业初期的筹备事宜,龚秀娟是蒋明锡接待并同意在会所上班的,之后,蒋明锡就离开四方会所回到深圳了,其他几名技师均没有见过蒋明锡,与蒋明锡没有任何联系。龚秀娟接受的是董超阳的控制和管理,退一步讲,即便龚秀娟有过卖淫行为,那么,她的行为也不是受到蒋明锡的管理和控制。
4、关于对技师龚秀娟的询问笔录证明效力的问题。
关于666号技师即龚秀娟的第三次笔录称“我去上班的时候蒋姓老板找我谈的,他问我之前是否做过色情服务,我说没有,他安排人教我的,提成也是他找我商谈的,面对面商谈的。”在龚秀娟的三次笔录中仅有一次,是这样说的,且龚秀娟的笔录与蒋明锡的笔录不一致,蒋明锡在供述中称其认识一个166号技师,后来将这名技师骂走了,并没有说还认识666号技师。辩护人认为在两人的笔录明显不一致的时候,不应当片面的听信一方的言辞,应当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在没有其他证据印证的情况下,不能认定龚秀娟的陈述就是属实的,况且以上内容并不是卖淫行为的事实。
三、董超阳与技师私自外出提供有偿性服务,应为董超阳与技师的个人行为,与蒋明锡无关。
根据案卷材料显示,在会所外发生的性交易行为,均是董超阳和技师个人的行为。而且,所得的嫖资都是董超阳与技师二人进行分成(注:并不是完全按照固定的比例,龚秀娟说和董超阳对半分,但也说客人给钱之后给董超阳300,巩凡凡说客人给她1500,给董超阳500)。没有交给龙向飞所管理的财务入账,这种情况不属于是会所的经营行为,而是董超阳与技师个人之间的擅自行为。四方会所的技师按要求都是不准外出到宾馆去服务,但在本案的证据材料中,有记载董超阳存在有带着技师到店外的宾馆进行服务的情况。但这些行为与四方会所无关,完全是董超阳利用其管理技师的便利,与技师私自外出提供服务而从中收取额外收入的个人行为,所得非法收入由董超阳和技师个人私分,这一部分收入没有进入到会所的财务账目当中。因此,会所内技师虽有在会所外为嫖客服务的行为,但这些行为都与会所无关,没有受到会所的控制与管理,更与蒋明锡无关。
综上所述,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蒋明锡构成组织卖淫罪,但没有充足证据证明蒋明锡具有组织卖淫的组织故意与组织行为,且在我国法律、司法解释没有明确将“手淫、口交、胸推”等行为纳入到组织卖淫罪中的卖淫行为范围之前,不宜对刑法中的卖淫概念作扩大解释,否则,违反了我国刑法关于罪刑法定的适用原则。因此,本辩护人建议法庭将每个被告人在本案中的具体行为进行区分,并按照刑法规定的组织卖淫罪的构成要件区别对待,依法宣告被告人蒋明锡无罪并立即释放。以维护我国刑法的正确适用,保护被告人的正当权益。
以上辩护意见,请法庭重视采纳。
辩护人:河南红达律师事务所
律 师: 谢建宏、娄珍杰